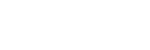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耳机成了甩不掉的“标配”,变成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。校园里,学生们戴着它走路、吃饭、听课,用声音筑起独处的围墙。
作为泰山科技学院的一名全生异科导师,周雨童不止一次在办公室听同事叹气:“现在的孩子,把自己关在耳机里,怎么沟通啊?”她也曾对着课桌上的签到表皱眉,时常望着这片“耳机森林”出神——那小小的设备,是否正在构筑师生间最遥远的距离?
这个疑问,在周雨童遇见李振宇同学后有了全新的答案。
初次见到振宇,是在今年新生入学后的第一次异科师生见面会上。他坐在离她较远的地方,黑色发带束着头发,耳朵上始终挂着一副黑色耳机,头微微低着,不参与讨论,也不与周围同学交流。
起初,周老师将这视为一种青春的叛逆或孤僻。但几次活动下来,一些矛盾的细节引起了她的注意:每当周雨童剖析就业创业案例的关键节点,或是解读《理想国》中的“洞穴寓言”时,他总会悄悄抬眼,眼神专注地跟随节奏;抛出问题时,他虽不发言,眉宇间却流露出认真的思索。

这种“沉默的专注”让周雨童越发困惑:既然听得如此投入,为何非要隔着一副耳机?她甚至私下找过他两次,想聊聊阅读感悟与个人规划,可他总是拘谨地点头,用“老师讲得很好”匆匆结束对话,耳机仿佛一道永不卸下的屏障。她一度认为,这或许是新时代师生间难以逾越的“数字鸿沟”。
直到11月初,一条周雨童师门群里的消息,打破了她们之间的沉默之墙。
学校非遗舞狮工坊接到了“省长杯”足球赛开幕式的表演任务,正为人手不足发愁。同时,她不由得想起去年运动会上那群少年舞狮时昂扬的“精气神”。周雨童希望能有更多同学体验到这种震撼,在协作拼搏中彼此成就。于是,她在群里发出了招募信息。

消息发出半小时,私聊框弹出了振宇的留言:“老师,我是残疾人,需佩助听器,能参加舞狮活动吗?有点心动。”
那一刻,周雨童握着手机的手僵住了,心中仿佛被重物撞击——原来,他一直戴着的不是隔绝世界的耳机,而是连接他与声音世界的桥梁。那些她曾误读的“孤僻”与“疏离”,不过是一个听障少年在用他自己的方式,小心翼翼守护着尊严。他坐在后排的沉默,不是心不在焉,而是要调动全部精力才能捕捉到声音的轨迹。一股强烈的愧疚感瞬间涌上心头,更生出沉甸甸的责任——必须帮这个孩子,抓住他眼中那束微弱却明亮的光。
周雨童立刻拨通了舞狮工坊指导老师齐凯的电话,话没说完就被打断:“你说的是戴助听器的同学?我们副主理人就是先天性听力障碍,从小靠助听器生活,现在舞狮动作比谁都流畅,高难度的‘踩桩’都不在话下!”
她赶紧把这个消息转给振宇,附带一句:“振宇,有人已经为你走过这条路了,大胆去试!”几分钟后,他激动地回复“副主理也是!那我要参加!”

接下来的四天高强度的训练,只要没有工作安排,周老师都会去训练场陪伴他们。11月的天气已经转凉,但敢当书院与东岳书院的训练场地里总是热气蒸腾。振宇因为助听器在剧烈运动中容易脱落,不得不比其他队员付出更多努力。她常常看见他倾尽全力,用全身的细胞去感受每一个动作、每一个节拍。


最让周雨童动容的,是训练间隙的画面。当其他队员卸下狮头喝水谈笑时,只有振宇依然在角落重复着动作,双手始终虚托,仿佛永远捧着一个无形的狮头。因身高不太适合担任狮头,他总是一边练习狮头的动作,一边用羡慕而专注的目光追随着其他搭档的完美配合。而每当两人交流时,这个一米八几的高个子男孩,总会自然而然地弯下腰,侧过他的右耳,只为听清说的每一个字。
周雨童就在一旁,用手机为他们记录下点滴。有一次训练结束,振宇兴奋地演示学习成果,狮头在他手中上下翻飞,虽然动作仍带生涩,却充满了原始而蓬勃的力量。


11月10日,“省长杯”足球赛开幕式如期而至。阳光炽烈,六头色彩艳丽的雄狮在绿茵场上格外醒目。观众席座无虚席,欢呼声与震天的鼓乐交织。周老师站在场边,看着队员们精彩亮相,狮身在阳光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芒。
然而,因战术与角色安排,振宇最终未能登台。他站在替补区,双手紧握成拳,目光却像被磁石吸住一般,紧紧追随着场上的每一个腾挪跳跃。
演出圆满结束。人潮渐散时,振宇跑到周雨童面前,汗水还挂在他的睫毛上。
“童姐,”他第一次这样叫,笑容坦然而明亮,“虽然没能上场,但这次训练让我知道,我可以。而且我很有收获,这就足够啦。”
没有电影《雄狮少年》里那种替补逆袭、万众欢呼的热血结局,那个下午的夕阳,也只是平静地为训练场拉出长长的影子。但就在那一刻,周雨童与学生们共读《理想国》时,柏拉图笔下那关于“勇气”的抽象论述,突然拥有了最坚实、最温热的载体。真正的勇气,不是聚光灯下赢得喝彩的瞬间,而是清晨训练场里,那个明知是替补却依然孤身加练的身影;是听不清鼓点,便将身躯贴近大地、用灵魂感知震颤的执着;是最终未能登场,却目光澄澈,笑着说“我已收获”的坦然。
振宇用他的“耳机”,让周雨童听见了沉默背后的渴望,也让她读懂了全生异科导师的真正意义——不是站在讲台上引导,是蹲下来倾听;不是预设成长的剧本,是陪着他在真实里前行。
振宇的“耳机”,也成了周雨童异科导师生涯里的一面镜子。现在再看到学生戴“耳机”,她不会再轻易贴上“封闭”的标签。或许是他们的“助听器”,或许是缓解焦虑的方式,或许只是想在嘈杂中保留一方思考的空间。


这份因“看见”而生的理解,也延续到与其他学生的互动中。面对敏感内向的瑞珂,周雨童在她夜训时默默守候,用一杯热牛奶和写着“别内耗,随时抱抱”的巧克力,温暖她孤独的内心;对于思维敏捷、善于表达的一乾,周老师则鼓励并指导她在“无用杯”通识素养大赛中撰写论文,让她的才华在更广阔的平台上荣获校级二等奖。
全生异科导师制的核心,从来不是“管理”与“塑造”,而是“看见”每一个生命独特的纹路,并珍视这纹路所带来的无限可能。
如今,周雨童时常回想起振宇弯下腰,将戴着助听器的右耳倾向她的样子。那个姿态,恰恰成了对异科导师工作最深刻的理解:教育的真谛,或许就藏在这温柔的俯身与平等的倾听之中。努力去聆听耳机另一侧的寂静,最终,却在寂静中照见了彼此的生命——那不是单方面的唤醒与塑造,而是两个灵魂的相互叩问与彼此照亮。

在这个师生共同构建的“理想国”里,最重要的不是宏伟的蓝图,而是在每一个看似微小的“看见”中,让师生共同体的根须,扎向更温暖、更坚韧的土壤。